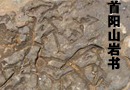|
送浩然上路
刘锡诚
昨天早晨儿子刘方发来邮件,说《北京晨报》的记者朋友告知,作家浩然逝世了。近年来,文艺界的前辈和同辈接二连三走得太多了,好似进入了一个送终的时代。浩然卧病多年,见阎王爷自是早晚的事,听到他辞世的噩耗,心里也就没有特别的震惊和悲痛,只是觉得十分可惜,中国文坛上少了一个终生为农民造像、以其作品见证了中国农村一段历史、称得上是农民朋友的作家。
我最后一次见到浩然,是2004年11月21日上午,在冯骥才为募集民间文化抢救保护基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个人画展和义卖会上。以往,在我眼里,现代文学馆实在只不过是文学界小圈子里一个活动的场所,那天,来文学馆参观的文坛名流和一般读者却很多,与其说是来参观冯骥才的画,不如说是为大冯的人格所打动,仰慕大冯为默默无闻的中国老百姓创作和传承的民间文化的保护所显示的中国文人气度。在电梯里,我和久未露面的浩然不期而遇。他是在家人的扶持下,拖着病体来到现代文学馆,为冯骥才的募集活动助威、打气的。我对浩然抱病来为大冯的公义活动呐喊助威既惊愕,又感动,一时不知所措。我问他的身体恢复得怎样,他很乐观地告诉我,恢复得还不错,说话虽然还有些迟钝,这不是能出来参加活动了?看得出来,他的行动多少有些艰难,说起话来也比常人慢。电梯的门开了,熙熙攘攘的人流把我们的谈话中断了。我为他身体状况的复原高兴和祝福。
浩然早年作为《中苏友好报》的编辑,曾下放在我的故乡山东省昌乐县东村,在那里当过村支部书记,领导过农业生产和社会改造,与农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那里写了一批短篇小说,后来写的长篇《艳阳天》所以大获成功,再现了当时的中国农村世态,生活气息浓厚,人物呼之欲出,也与在东村的生活体验分不开。他把昌乐称为他的“第二故乡”。20世纪80年代,家乡建了一座酒店,就命名为“艳阳天大酒店”。多年来,除了我作为文学刊物的编辑与作家的交往外,还有这层乡土的关系,使我与浩然有一种亲近感。在建国50周年时,家乡昌乐政协编了一本《浩然与昌乐》,收了一些昌乐的作者写的与浩然交往的文章以及浩然写的与昌乐有关的作品。浩然给我打来电话,要我为这本书写个序。无论是看在家乡父老的份儿上,还是看在多年来与浩然的文学交往的份儿上,我都是义不容辞的。我把这份差事答应下来了。我写了大致如下的一段文字。
大凡稍稍研究过浩然的作品和经历的人,都会知道,他所以能写出享誉一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及一批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所以能塑造出一大批各色各样的60年代的农民形象,与三年困难时期他在昌乐县的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有着莫大的关系。没有1960年在前东村劳动锻炼、当支部书记的那段经历,没有与东村农民兄弟的那种情深似海的交往和生死与共的生活,就不会有取得后来那样的文学成就的浩然。我从文集中看到的是一个有责任感、有良知的作家。浩然把昌乐当成他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他不忘昌乐这块贫瘠而富饶的土地所给予他的恩惠。他不忘那些在饥饿的夜晚把一碗地瓜面粥省给他的农民兄弟。正如他说的,一口饭就能救一个生命。没有这种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的人,就难说他了解农民。当然,除了昌乐外,浩然还有其他距京城更近的生活基地,如河北的三河县。我相信,在作家队伍里,浩然是为数不多的知根知底地了解农民的作家之一。我从这里悟出了,为什么昌乐人总是记着浩然,惦着浩然,想着浩然,敬着浩然。浩然是个有成就的作家,也是个容易被人误解的作家。正如世界上没有完人一样,浩然也是从坎坷中走过来的。他有个时候甚至是遍体鳞伤的。是改革开放及其成就,使他“那么快地挣扎起来”了。这也许成了他的人生财富。新时期初期,我在《文艺报》工作的时候,曾于1980年3月15日开过一次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邀请他与会参加讨论。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对农民和农村怀着很深的感情。那次座谈会是我策划的,并为那次座谈会想出了一个 “文学,要关心九亿农民”的口号。那次会由已故的老主编冯牧主持。刘绍棠、管桦、林斤澜来了,浩然也来了,并在会上发了言。他的发言很动情。很久不在公开场合下露面的浩然,那时忍受着舆论的和心理的双重压力,我们邀请他与会,表明了我们对他的作品的评价和对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态度。
浩然在会上说:“这个会很重要,是为九亿农民征求精神食粮的会议。文学艺术不仅要对九亿农民发挥作用,还有一个形象而准确地介绍农村情况和农民面貌的作用。这30 年来,农村变化很大。历史上哪一次农民运动也不像这30年的农民运动——如果把农业合作化当作一次农民运动的话——翻天覆地,触动每一个人,广泛、激烈而深刻,生活既丰富多彩又十分复杂。对30年的各个阶段要做具体分析。作家要站在高高的山巅上。要重感情,但不要感情用事。这30年的农民运动,从整体上讲,从根本上讲,给中国九亿农民带来了好处:他们不受剥削了,不受兵荒马乱的严重骚扰了。这是过去任何朝代、任何政党所不能给予他们的。这是主流。逃荒要饭,只是暂时和局部的现象。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是这样反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更多的益处,不会有那些灾难和痛苦。这是我近两三年来经过痛苦的反省过程之后,准备再写东西时考虑得出的基调。我过去一直是紧跟政策的。但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还没有去写那种浮夸的、胡说八道的东西,作品也有点生活气息。虽然我生活在农民中间,由于受着一种思想的束缚,我看农民的欢乐多了,看他们的痛苦少了,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生活的,所以我没能像有的同志那样写出好作品来。今后怎么办?要重新认识生活,首先要重新认识我自己。农民受到精神和经济上的灾害是不小的。文学可以起到影响农民的灵魂、医治农民精神创伤的作用,从而指导他们的生活。文学特别需要替农民说说话,起点舆论作用;应该狠狠揭露和鞭打那些不心疼农民的人!这种人很不少,官僚主义、霸道作风,相当严重。《文艺报》召开这个会,要推动一下农村题材的创作,很符合我的心愿。我是受了内伤的。我再不想去图解任何概念了,我要到生活中去,用我的信仰——只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用我的良心——忠实于养育我的农民,去了解农民,描写农民,替农民说话。好的,我歌颂;坏的,就揭露。身体条件差了,我不能“大面积垦荒’了,只能勤恳地去经营我的‘两垅地’。就此拉秧,还不甘心,我还要努力再开一茬小花。”
听着浩然的发言,我感到了他心灵深处的激荡,了解了由“内伤”带来的痛楚。也对他在农民问题上的责任感和同情感抱有认同感。我希望他甩掉包袱,再为农民兄弟写出一些作品来。20世纪90年代,低调生活的他,终于又写出了一部长篇《苍生》。《苍生》大概就是他所心中的那“一茬小花”中的一株吧。
有感于浩然,我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不同的作家评论家,在农民和农村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见解是必然的,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现在要分析农村的社会人际关系,也许比以往更为复杂。但没有对今日农村的社会人际关系的正确分析和把握,就很难进入创作,即使进入了创作过程,也很难写出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的优秀作品来。这是常识。现在,农民和农村问题仍然是作家们应该关注的大问题,毕竟我们还是个农业大国,还是个农业人口大国!可是,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作家太少了!抱着热情和同情来关心农民和农村的作家就更少得可怜了!”
浩然老兄,是是非非,爱恨情仇,都撇在一边了,安然地上路吧!
2008年2月22日
|